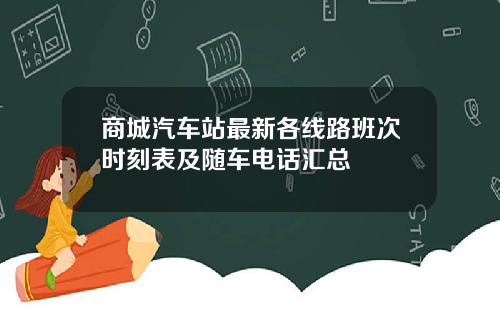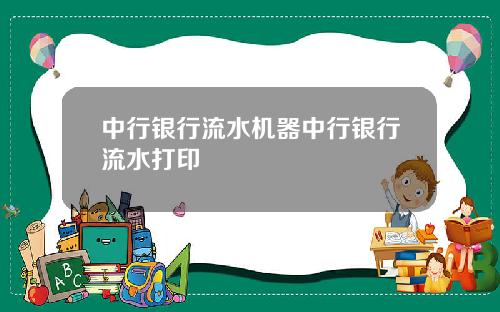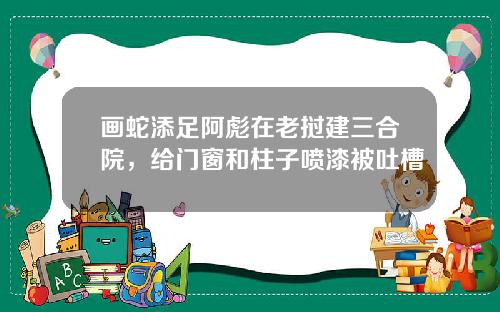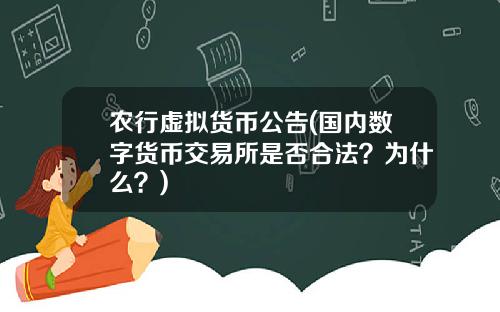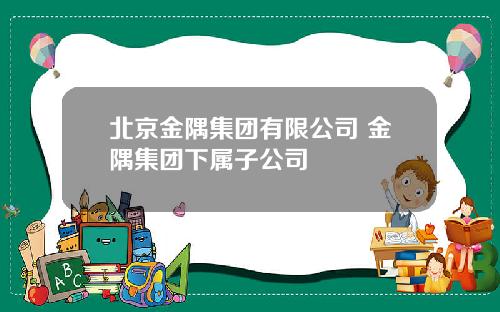花鸟画自魏晋南北朝初具雏形以来,延及北宋中期,出现了第一个繁荣阶段。同时,由于风格富丽的黄筌画派受帝王青睐,统治画院一百多年,致使逐渐形成迟滞局面。而北宋中期的花鸟画变革,突破黄家体制,从根本上转变了花鸟画坛因循守旧的颓风,为此后花鸟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易元吉的猿猴图在这场变革中的作用,被历代画史研究者所肯定。可以这样说,正是易元吉通过前人少有涉及的猿猴题材,和贴近自然的写生实践,阐发了徐熙画派的野逸追求,推动了诸多画家和士大夫对花鸟画进行重新审视,从而开始扭转北宋立国以来,推崇“黄家富贵”、轻视“徐熙野逸”的局面。虽然易元吉为此“竟为人鸩”,但是稍后的改革派画家崔白,汲取了易元吉血的教训,他在朝廷破格授予艺学之职时,坚辞不受,终得“特免雷同差遣,非御前有旨毋召”,从而避免了画院中守旧派画家的迫害,也保证了北宋中期花鸟画变革得以最后成功。
时代语境与生平事略
易元吉,字庆之,长沙人,生年已不可考,卒年大约在1064年前后,即北宋仁宗和英宗时期。这是北宋王朝实现重大转捩的历史阶段,政治、思想和文化均出现了重大变革,而易元吉的猿猴画正是这一变革时期花鸟画嬗变的产物。
北宋诗人邵雍在《插花吟》中,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称为盛世,所谓“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然而,繁华背后却隐含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文人士大夫中的开明人士,为挽救时局,提出了各种主张并努力实践之。
思想上,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对儒学进行了哲学化的改造,将儒家的仁义道德上升为天理,建立了囊括天人关系的新儒学(即理学),对北宋哲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政治上,宋仁宗采纳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意见,施行新政。宋英宗继续重用改革派大臣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而至宋神宗时期,更是任用王安石进行较为全面的变法。虽然这些新政由于触及贵族官僚的利益,最后不得不终止,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宋中期花鸟画坛的嬗变。
北宋初年,黄筌画派成为皇家画院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懂画能画的文人士大夫,主张突破儒家思想中“以德比附”的传统观念,走向抒情言志,注重追求作品的神韵意趣,对黄家体制则不以为然。欧阳修认为:“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他提出重“神意”轻“形似”的主张。米芾认为黄筌花鸟画“虽富艳皆俗”,表达了士大夫们对黄家体制的不满和轻蔑。于是,北宋中期的花鸟画领域出现了旨在突破黄家体制、探寻花鸟画新模式的变革。其中,赵昌起到了先驱的作用,他竭力探索新的表现技法;而易元吉则深受赵昌画风影响,力主改革画院中因袭的陋习。
然而不幸的是,易元吉为艺术上的革新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根据《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画史》和《图绘宝鉴》等史料的记载可知,易元吉原是一名出身卑微的民间画工,“灵机深敏,画制优长;花鸟蜂蝉,动臻精奥”,早年即在花鸟画创作方面取得了相当高的造诣,“善画得名于时”。后来,他看到了稍早于他的花鸟画家赵昌的作品,赞叹不已,感到自己难以超越,于是“志欲以古人所未到者驰其名”,选择了猿猴画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易元吉遍访名山大川,不顾个人安危,近距离观察猿猴在山野之中的身形姿态,经过多年的刻苦研习,终于自成一家。其所绘猿猴獐鹿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写动植之状,无出其右者”,为“世俗之所不得窥其藩”。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刘元瑜爱惜易元吉的才华,特意将他破格提拔为州学助教(从九品)。易元吉很珍惜这个极为难得的职位,常在画作中题识“长沙助教易元吉画”“潭散吏易元吉作”等字样。嘉祐三年(1058),朝廷以刘元瑜“擅补画工易元吉为画助教”为由,将他降职为随州知州,易元吉也被迫离开湖南。此后,易元吉游历余杭、开封等地。在京师,他结识了童贯的父亲童湜,并得到他的资助。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汴京城景灵宫孝严殿落成,皇帝“召(易)元吉画迎厘齐殿御扆,其中扇画太湖石,仍写都下有名鹁鸽及雒中名花,其两侧扇画孔雀。又于神游殿之小屏画牙獐,皆极其思”。易元吉艺压群僚,名声大振。他深厚的艺术造诣和自然生动的绘画风格,使画院中恪守黄家体制的画师们相形见绌,不免嫉恨。易元吉有凭藉才华改革画院因袭陋习的素志。对于这次蒙召进入皇家画院,他十分重视,认为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来了,表示“吾平生至艺,于是有所显发矣!”不久,皇帝诏命易元吉在开先殿西厢绘制《百猿图》,特许其先领“粉墨之资二百千”,使易元吉得以施展其所学。但是,易元吉只画了十多只猿猴就突然去世了。他的死因是画史疑案之一,《宣和画谱》认为易元吉是染时疫而病故,而米芾在《画史》中却记载道:“画严孝殿壁,画院人嫉其能,只令其画獐猿,竟为人鸩。”认为画院中嫉贤妒能的黄派末流下毒暗害了易元吉。结合当时画院的情况分析,米芾的观点应当是相对可信的。著名学者徐建融也持此观点。
艺术风格及画迹
易元吉的绘画才能是多方面的,花鸟、走兽、杂物、山水均有涉及,且别开生面、莫不精湛,而他的猿猴图成就最高,在当时就已备受世人瞩目,引得诗人纷纷题咏:“易老笔精湖海推,画意忘形形更奇”,“悬之门堂阅疑真,妙哉易生笔有神”。而米芾在《画史》中更是把他推崇为“徐熙后一人而已”,不仅肯定了易元吉的艺术成就,也道出了易元吉猿猴图的基本风貌,即和徐熙花鸟画一样具有野逸意蕴。
易元吉猿猴图的野逸意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意境上,追求清新野逸。易元吉的猿猴图突破了黄筌画派珍禽奇花的表现题材,将目光投向宫墙之外的广阔天地,通过描绘山野中猿猴这一鲜活灵动的生命,和大自然建立起某种灵感上的联系。易元吉的猿猴图,与徐熙画派画家所热衷于表现的凫雁芦花、败荷野草以及梅兰竹菊一样,都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胸臆和襟怀,故而得到文人画家米芾的高度赞赏。北宋文学家、词人秦观《观易元吉獐猿图歌》云:“参天老木相樛枝,嵌空怪石衔青漪。两猿上下一旁挂,两猿熟视苍蛙疑。萧萧丛竹山风吹,海棠杜宇相因依。”将易元吉猿猴图的野逸意蕴描绘得淋漓尽致。
笔墨上,突破黄家体制的勾填法限制,淡彩薄敷,尽显水墨意趣。宋代沈括曾形容徐熙花鸟画:“以墨笔为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这种画法不屑于细笔勾勒、填彩晕染,而墨写花草翎毛,略施杂彩,时人称作“落墨花”。米芾将易元吉猿猴图中类似的笔法称作“逸色笔”。如果将最能体现徐熙野逸风格的《雪竹图》和传世的易元吉猿猴图作一比较,不难看出两者之间在艺术风格上的相通之处。
易元吉一生勤奋,创作了大量的花鸟画作品,仅《宣和画谱》所记载的北宋御府收藏的他的作品就有245幅,其中猿猴图40幅。然而,随着“靖康之难”,金兵攻入北宋都城,御府所藏易元吉的猿猴图大多不知所终。流传至今并被书画界和学术界首肯的易元吉猿猴图作品极少,有《猴猫图》《聚猿图》和《枇杷猿戏图》等,其中《猴猫图》是可以确认的易元吉猿猴图真迹,而另外两件则真赝尚有争议,但可以作为研究易元吉猿猴图的参考资料。
猴猫图
《猴猫图》,绢本设色,纵31.9厘米,横57.2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虽然没有易元吉款印,但画幅左上方有宋徽宗瘦金体签题“易元吉猴猫图”,并有“宣和中秘”和“内府图书之印”等印,拖尾有赵孟頫、张锡等人的题跋。这幅画是唯一被书画界和学术界所公认的易元吉真迹,图绘一只脖子上围缚着粗绳的猕猴,虽为石柱所系,却顽皮本性未泯,突然恶作剧似地将路过的狸猫揽入怀中,而另一只狸猫惊惧地避让回顾。两只狸猫的脖子上都系有丝带,显然是富贵人家饲养的宠物,据此推测,此图应当是易元吉在宫廷或某位官宦人家写生宠物而得。猕猴和狸猫都是天性灵敏之物,极难描绘,而易元吉却能将两者的神情表现得如此逼真——猕猴的得意,怀中狸猫的抗拒,避退一旁的狸猫全身拱起、愤怒而又警戒的神态,让人叹为观止。难怪张锡曾赞叹:“今观易元吉所画二物,入圣造微,俨有奔动气象,又在李迪之上,信宋院人神品也。”此图的笔墨技法,体现了易元吉猿猴图的基本风貌,猕猴和狸猫的毫毛先用纤细笔触细细勾出,密而不乱、毛绒蓬松,极具质感,然后略加晕染、敷以淡彩,清逸秀雅。
《聚猿图》,绢本水墨,纵39.3厘米,横146厘米,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无款印,有南宋贾似道,清代耿昭忠、安岐、乾隆帝的收传印,拖纸有元代钱选题跋。图绘20余只猿猴栖息嬉戏于山壑深处的情景——幽深山谷,溪水汩汩,众猿猴或栖息枝头、或穿行山涧、或搔痒自娱、或嬉戏亲昵,极尽野逸姿态,意趣盎然。笔墨技法已有明清写意画的意趣,黑猿用浓墨点染而成,树木山石则用浓淡墨绘就。易元吉仅用墨色就将群猿的天性表露无遗,堪称两宋画猿猴之第一人。
枇杷猿戏图
《枇杷猿戏图》,绢本设色,纵165厘米,横107.9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图没有款印,《宣和画谱》所著录的易元吉《枇杷猿戏图》大概是这一幅,款印应当是在重新装裱时裁去了,《石渠宝笈初编》和《故宫书画图录》均收录了此图。图绘两只黑猿停栖于枇杷树的枝干之上,一只稳坐于粗壮苍劲的主干上,神情安逸,另一只则伸着长长的手臂,调皮地攀附在垂坠的枝条上,回首顾盼主干上的黑猿;两只黑猿,四目相对,含笑相望。画面所展示的极具人情意味的瞬间,使人不得不赞叹画家对自然观察的细致入微,以及深厚的写实功力。
此外,传为易元吉所作的猿猴图还有《乔柯猿挂图》《猿鹿图》《三猿捕鹭图》《蛛网攫猿图》《猿猴摘果图》《缚猴窃果图》《树上二猿图》和《獐猿图》等。
乔柯猿挂图
猿鹿图
三猿捕鹭图
蛛网攫猿图
猿猴摘果图
绘画史地位及影响
猿猴很早就被艺术家们所关注。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铜灯和山东曲阜出土的战国带钩上都有猿猴的造型,汉代画像砖上也有牵狗玩猴的图案。画史记载,东晋戴逵绘有《胡人弄猿图》,唐代边鸾绘有《石榴猴鼠图》。文学作品中,三国阮籍写有《猕猴赋》,西晋傅弦写有《猿猴赋》,此外,唐代诗人杜甫《登高》《秋兴八首》、王昌龄《送魏二》和白居易《琵琶行》中,均有提及猿猴。其中,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文学作品中,猿猴乃至“猿啼”“猿吟”,均是文人失意愁苦心绪的载体。而易元吉创作的猿猴图,不仅将猿猴拟人化、赋予它们人的思想和情趣,而且还着重表达了猿猴天真自然、顽皮灵动的一面,令人耳目一新,改变了以往猿猴低沉哀怨的形象,给人以极大的艺术审美享受。传为易元吉所作的《三猿捕鹭图》,更是寓含着人们科举及第的祈愿,图中三只猿猴高居古树之上招引白鹭,三猿谐音“三元”,即指科举考试中乡试、会试和殿试的第一名,分别为解元、会元和状元。三元及第几乎是每个读书人的志向,这种祥瑞意趣是易元吉之前的猿猴题材绘画作品所没有的。可以这样说,易元吉的猿猴图丰富了作为文学艺术载体的猿猴形象的内涵。
就中国花鸟画发展史而言,易元吉的猿猴图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推动了北宋中期花鸟画的嬗变。
北宋中期,主导皇家画院的黄筌画派几乎成了一种僵化的定律。邓椿《画继》记载:“图画院四方召试者源源而来,多有不合而去者。盖一时所尚,专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则谓不合法度,或无师承,故所作止众工之事,不能高也。”画院画师大多只知在皇宫内苑描绘奇花瑞兽,甚至因袭临摹黄筌父子的作品,花鸟画坛出现了墨守成规、陈陈相因、毫无生气的局面。而易元吉的猿猴图,以独辟蹊径的题材开拓和追捕野逸天性的写生经历,推动了北宋中期的花鸟画变革。
花鸟画自唐代独立成科以来,经过五代和北宋初期的发展,已经臻于成熟,不仅技法自成体系,而且名家辈出,譬如边鸾、滕昌祐、刁光胤、徐熙、黄筌、赵昌等。显然,要冲破黄筌画派那套似乎几近完美的程式化范式,必须在题材上另寻蹊径,去挖掘前人尚未认识到或认识不深的领域。易元吉说:“世未乏人,要须摆脱旧习,超轶古人之所未到,则可以谓名家。”于是,他大胆地选择了在家乡山野中常见的猿猴,作为自己造就绘画艺术新高峰的载体。
易元吉的写生,使得因循守旧的黄家画派画师相形见绌,即使和赵昌、曾云巢这些注重写生的画家相比,也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他写生重在捕捉猿猴天性野逸的真性情,经常出入深山老林,备尝艰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近距离地观察猿猴獐鹿的天纵之姿,动辄数月,为他的猿猴图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形象素材和生活经验。正如《宣和画谱》所记载:“(易元吉)游于荆湖间,搜奇访古,名山大川每遇胜丽佳处,辄留其意,几与猿狖鹿豕同游,故心传目击之妙,一写于毫端间,则是世俗之所不得窥其藩也。”
易元吉的猿猴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以其新颖的题材和清雅的风格,在两宋时期就备受画坛推崇。北宋刘挚的《易元吉画猿》、黄庭坚的《易生画獐猿猴赞》、秦观的《观易元吉獐猿图歌》、张来的《獐猿图》,以及南宋范成大的《题易元吉獐猿两图》,均认为易元吉的猿猴图“妙哉易生笔有神”。易元吉将猿猴作为中国画的重要题材,丰富了花鸟画内容,拓展了花鸟画领域。自宋元以降,历代在猿猴图创作上颇有建树的画家,大多受易元吉的影响。供职于北宋神宗画院的丁贶,画花鸟近于易元吉一路;文人画家晁补之,猿猴獐鹿专学易元吉;南宋画家陈善,花鸟獐猿学易元吉,赋色清淡,颇能逼真。传世的元代颜辉的《猿图》和清代沈铨的《蜂猴图》,也均有易元吉猿猴图的痕迹。近现代画家张大千十分喜爱易元吉的猿猴图,曾画过一幅临摹自易元吉作品的工笔设色画《檞树双猿图》。
显然,易元吉的猿猴图不仅在宋元时期,而且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也必将为当今花鸟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这正是我们梳理易元吉猿猴图演绎过程的意义所在。
“传神写戏狙”是乾隆皇帝在易元吉《聚猿图》上题诗的诗句。狙:古书上指一种猴子。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