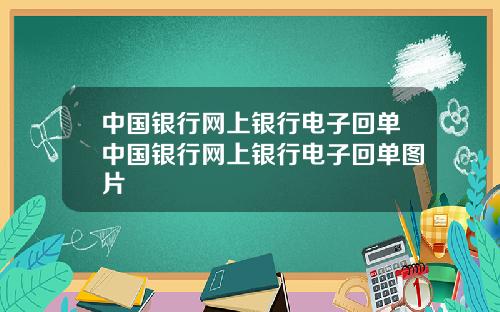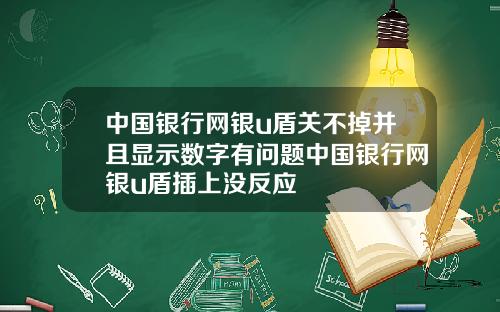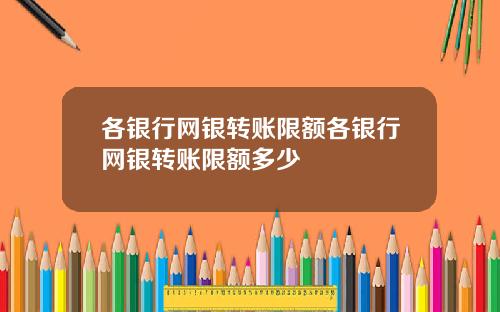改换门庭,投靠使馆
池步洲一九三二年初冬结婚,一九三四年晚春有了一个长女,起了个日本女名叫美惠子,中国名字就叫池惠美。一九三五年仲夏,又有了长子哲雄。在儿子满月和周岁这两个中国人认为值得庆贺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的福州同乡、同学都来祝贺,并拍有纪念照片,照片上,大大小小不下三十几人之多。这些人后来大都回国参加抗日,命运则几乎都不大好。
这期间,福州人萧叔宣[4]与周孝培到驻日大使馆武官署担任正副武官。按照规定,驻外武官必须每月上交政府一篇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分析报告。他们初来乍到,情况不熟,难于下笔。周孝培看到《留东学报》上池步洲写的文章,颇为欣赏,就通过同乡人的关系找到池步洲,要他代写这一报告,答应每月支给津贴三十日元(这个数目,在当时来说已经不算小了)。于是池步洲广泛注意各报刊,每月写出一篇四五千字的报告上交,双方皆大欢喜。
国民党政府的办事机构相当精简,人员并不很多,根本就没有什么专职的秘书、翻译之类。几个见习武官,反正是“见习”,手中无权,每人却都有固定的薪俸和不固定的“活动经费”,乐得各自为政,除常规会议外,很少到武官署来。
驻外使馆的武官,同时兼任军事情报的搜集工作,是公开的秘密。正副武官和见习武官,都有一笔“活动经费”,用来豢养若干名情报搜集人员。这些提供情报的“眼线”或曰“情报贩子”,大多数是日本人,也有少数是与日本军方有关联的中国人,但无一例外都是“直线联系”,没有人会傻乎乎地跑到武官署里面来。
驻日武官署内,除了正副武官,平时只有两三个人办公,每天要办的公务倒不少。其中有一位叶老先生,五十多岁了,是个老华侨,妻子是日本人,精通日语,在武官署承办一些日文文案,但是中文根底较差,根本没有写作中文报告的能力。遇到有急需翻译的日文资料,周孝培就拿来请池步洲干。开头不过是义务劳动,后来觉得武官署人手实在太少,就想聘请池步洲为雇员,月薪一百五十日元。这数字,比在监督处要高一倍还多。一九三五年的九、十月间,池步洲终于辞去了监督处的工作,正式到武官署上班了。
池步洲正式到武官署上班,和叶老先生对面而坐。叶先生办理日文文档,池步洲办理中文文档,分工明确,各不相扰。
池步洲到了武官署之后,才发现还有一位上校军衔的海军武官,名叫刘田甫,原来就是他在葫芦岛海军学校时代的校长。不过刘武官很少到武官署来,得知池步洲是他原来的学生,如今在异国他乡不期而遇,只是表示喜悦而已,却从来没让池步洲为他做什么。看起来,陆军与海军之间,似乎也有明显的矛盾。
各国派驻东京的大使馆,经常举办一些宴会、舞会,招待别的使馆人员。池步洲在武官署虽然是雇员的身份,却也常常接到这样的邀请。
各国的驻东京使馆,都编有一本使馆人员名册,分发给各国使馆,用来作为邀请参加宴会、舞会的人员依据。这种名册,没有人员变动,就要更换,有时候一月换一次,有时候一月换几次。这种名册,不论大使、参赞、秘书及各级职员,都有“夫人姓名”这一项。但是中国大使馆的人员名册,在各人的“夫人姓名”栏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写着absent(不在)。
其实,所有使馆的工作人员,几乎都带着夫人随任的。不但萧、周两位武官的夫人连同子女举家随任,许世英大使的夫人,也在使馆居住,这是完全公开的事情,并不是秘密。那么,为什么名册上都要写上absent呢?原因就是这些夫人们大都不会外语(英语、日语),也不会跳舞,更不懂得国际性交往的礼仪。特别是许大使的夫人,还是小脚,典型的“土包子”。所以,在使馆人员名册上写明“夫人不在”,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别国使馆的邀请。
池步洲虽然有夫人,却也“按例”在名册上写着“夫人不在”。有一次,他和十几条“假光棍儿”一同去参加英国大使馆的招待会,目的无非是想到这样的场合见识见识。他们刚到英国大使馆客厅门口,就有一位小姐拿着一个口袋迎上前来,要大家“摸彩”。大家还以为是摸纪念品呢。
等到摸出来一看,竟是一位太太或小姐的芳名——原来,这是使馆专门为单身男宾请来的“陪侍”,而且是“外交惯例”。这些小姐或太太,第一都会说英语和日语,第二都善于辞令、长于跳舞,第三还都楚楚动人,风度翩翩,第四据说大都是英国来东京留学的学生或英国旅日侨眷。
那一回,池步洲被一位英国太太拉着在舞池里转了好几个圈,也踩了人家好几脚,出足了洋相。从此,他这个地道的土包子,再也不敢去参加诸如此类的国际性社交活动了。
池步洲到武官署上班不久,就到了一九三六年元旦,照例休息过年。但是这时候日本政局动荡,流言四起,都说日本的少壮派军人要发动军事政变。此事与中国留学生关系不是太大,但对中国驻日武官署而言,却是天大的大事,所有情报人员倾巢出动,刺探“内部消息”,往国内传送。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日本东京的天空黑云密布。一连下了三个晚上大雪,一尺多厚的积雪,已经严严地覆盖了全城。这是五十四年来不遇的大雪,而且看样子还要下。
披上了银装的东京,既有东方色彩,又有西方色彩。离皇宫几百米的地方,是一座四层的钢筋水泥结构的新式建筑。这是处理宫廷事务和天皇办公的宫内省大厦。在紧靠皇宫的一座小山后面,是一幢幢政府官员的官邸,其中最大的是首相官邸。
夜深了,可是外表宁静的东京,却酝酿着一场激烈的骚动。在皇宫外侧一端,是第一师团的兵营。由于陆军省(相当于中国的“部”)一名少佐告密说:有人要发动武装叛乱。这当然引起了当局对这个兵营的严密注意。嫌疑分子已经受到监视,还给政府要员加派了保镖。政府大厦和官邸的门窗都用钢筋铁条加固,还安上了直通警视厅的报警器。
这一天安然无事。宪兵队和警方自以为可以从容应付局势,一小撮叛乱分子毕竟掀不起什么大浪来。
但是,就在此刻,这个负责守卫皇宫的精锐部队中的叛乱分子正在准备于次日拂晓前,分头袭击东京的六个目标,包括警视厅和若干政府官员的住宅。
二月二十六日清晨四时,香田清真大尉和其他政变领导人把他们的部下从梦中叫醒。士兵们对阴谋一无所知,他们还以为是进行一次夜间演习,各个小组立刻奔向了各自的目的地。香田自己率领的一组,将攻占陆军大臣官邸,想强迫高级将领支持他们。另一组将占领警视厅。其他四组则分别去刺杀首相、藏相(财政大臣)、宫内相和侍从长。
栗原中尉和一名宪兵军官直奔首相官邸正门,解除了在大门旁边室内睡觉的警察的武装,进入官邸。顿时,枪声大作,大厅内吊灯全被打碎。住在首相官邸后门外对面的迫水久常,既是首相的秘书,又是首相的女婿。他听到枪声,马上给警视厅挂电话。但是没人接听,因为警察已经被叛乱的陆军打退了。迫水第二次再给警视厅打电话,电话里说:“我们是起义部队。”五百名政变军人已占领了警视厅。他又给附近的宪兵队打电话。宪兵队不安地回答:“局势已经失去控制,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这时候,首相冈田启介被惊醒了。他的妹夫松尾传藏急忙把他引到一间密室里藏了起来。可是松尾刚走出来,就被冲上来的政变军误以为是首相,开枪打死了在离首相宫邸几条街口的地方,政变军人冲进陆军大臣川岛义之的官邸。香田大尉把川岛叫出来,向他提出一系列要求,川岛俯首听命,立即前往皇宫,向天皇启奏叛军的要求。
安藤辉三大尉率领的一百五十名士兵冲进天皇侍从长铃木的官邸。铃木被叛军打了好几枪,但都未击中要害,侥幸活了下来。
当叛军冲进藏相高桥是清的宽大卧室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睡觉。一名中尉握着手枪,一脚踢掉藏相的被子,喊一声:“天诛!”把枪中的全部子弹射向这位老人。另一名政变军官大喊一声跳上前来,挥起军刀砍去,用力太猛,透过高桥的棉衣,砍断了他的右臂,接着又把刀刺进藏相的腹部。藏相是陆军出身,又当上了日本银行的总裁和贵族院的议员。少壮派军官憎恨他,因为他坚持削减上一年的巨额军费。
还有一伙儿政变军由高桥太郎少尉率领闯进了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的郊区寓所。渡边正和他的小女儿躺在床上。高桥用手枪向他射击,然后再用军刀砍掉了他的脑袋。另一组叛乱者在山区休养地到处搜寻天皇心腹顾问牧野伸显。由于找不到他,叛军就放火焚烧旅馆,逼他出来。但是这位老人已经从后门逃上山去了。政变军紧追不舍,朝他打了一串子弹,误以为打中了,才一轰而去。同时,前首相斋藤实也被杀了。
天亮了,东京的市民们还被蒙在鼓里,直到警察让乘坐公共汽车的市民绕开皇宫和政府大楼,人们才感到事情不妙。这时候,暴力行动已经结束,政变军人占领了东京市中心约一平方英里的地方。他们利用山王旅馆作临时指挥部,把“尊王义军”的旗子挂在首相官邸外面。他们散发“宣言”,声称要“清君侧”,要粉碎重臣集团,认为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都是破坏国体的元凶。
这就是震惊全世界的“二·二六”暴乱暴乱事件的前后经过。
为什么在日本军队中会出现这种“下克上”的现象呢?原来日本军阀早就有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的野心。早在一九二一年夏天,首相田中义一就向天皇密奏,打算先征服满蒙,再侵略中国,然后征服全世界。在日本军队里,一派人认为不经过政变,也可以实现军事独裁和侵略中国的目的,主张放弃刺杀和政变计划。他们在陆军内叫做“统制派”。而另一部分下级青年军官,仍没有放弃发动政变刺杀大臣建立军事独裁的主张。他们被称作“皇道派”。“二·二六”政变暴乱,就是“皇道派”这帮青年军官干的。
“二二六”政变叛乱由于得不到其他部队的支持,最后只能投降。但是,法西斯势力不是因此减弱,而是进一步加强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在日本陆军中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得到了日本势力最大的四大财阀的支持,确定了全面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国策,进行扩军。这样,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体制,在“二·二六”暴乱之后最后确立起来了。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他们终于在中国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公开侵略中国,并由此拉开了世界大战的序幕。
“二·二六”事件前后,是中国驻日武官署最忙的时候。萧武官通过他的情报网,迅速获得了上述情报。但是原本都是日文,而且篇幅不少,需要连夜整理、翻译,第二天天明就要派一名见习武官专程回国送达国民政府。这一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池步洲的身上。他通宵达旦地坐在办公桌旁奋笔疾书,萧武官就在办公室坐镇等待。池步洲写出一页,他看一页。经过一日一夜的连续奋战,好几万字的报告终于整理、翻译完毕,并安全地送回国内。对国民政府来说,通过这样的情报,可以判断日本帝国主义的动向,当然是十分重要的。
一九三六年,南京政府鉴于中日关系紧张,任命许世英为中国驻日大使。这个许世英,也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虽然并不懂得日语,但是却是日本政界人物有所交往;虽然不是“强硬派”人物,却也绝不是“投降派”人物。在那个“弱国无外交”的年代,他能够挺直了脊梁说话,就算是很不简单了。也正是因为有他出任驻日大使,抗战事起,才会有那么多爱国志士在他的支持下回国抗日。
许世英(1873-1964),字俊人,一作静仁,晚年别号双溪老人,至德县兆吉山(今安徽东至县)官港乡许村人。十九岁中秀才,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拨贡生选送京师参加廷试,得一等,以七品京官分发刑部,历任浙江司副主稿,直隶司、四川司主稿和刑部主事(六品)。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京师城外巡警厅佥事。从此跻身官场,历经晚清、北洋、民国三个时期,宦海浮游六十余年,成为我国近代政坛上的一位著名历史人物。
晚清时代,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光绪出奔西安,在两宫回銮时,许世英随驾护行,一手承办沿途刑案。由于护驾有功,一九○六年年终考绩,被列为京察一等,得以四品官任用。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宣布东三省改行新制,设立省的建制,任徐世昌为第一任东三省总督,许世英以“随员”身份同往东三省,后被任命为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相当于高级法院院长)。此后,许世英在全国司法界崭露头角,并被视为司法“专才”。宣统二年(1910),清廷委任徐谦为正代表,许世英为副代表,赴美国华盛顿参加万国司法制度及改良监狱会议,会后考察欧美十国司法制度。回国后,任山西提法使,旋任布政使。
许世英曾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赞许。辛亥革命中,许与山西巡抚张锡銮等联名呼吁清帝退位,赞同建立民国。
民国六年(1917),许世英由大理院院长转任司法总长,确立律师制度,设置新法庭等,深得孙先生嘉许,称为“司法革命”。
民国十三年(1924),北方军队酝酿倒曹拥段,许世英认为曹锟必倒,但应对纷争之局有预筹,于是密陈段氏非取得孙中山合作不可,并自任密使南下广东与孙中山密谈。孙中山面允许世英,候曹锟退位,段祺瑞入都,朝电相邀,夕即北上。孙中山指着许对人说:“许先生北方第一人也!”又说他:“俊人与予研究主义学说、方略,处处有远大理想,咀嚼精华,决不是猪八戒吃人参果。”许世英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极为敬佩,认为“天下为公”,定能团结民众,唤起民众,成为中华的支柱,还密带数十册《三民主义》回到北平,传播孙文学说。
后中山先生病逝,段祺瑞改组临时政府,增设国务院,许世英出任总理。
一九二一年,许世英出任安徽省省长,裁去武军四十八营,宣布军阀操纵贿选的省议会选举无效;创办安徽法政学堂,注意培养人才,资送数人赴日留学。但当时马联甲拥兵驻蚌,另派劲旅坐镇省会,对许世英掣肘威胁,无法施展抱负,不得不于一九三二年愤而辞职。
三十年代初,黄山因交通不便,游人稀少,再加之连年灾害,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时任黄山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许世英,接到报告后,先期派员到黄山勘查。得知灾情确实严重,即于五月十九日从上海启程,专赴黄山察看灾情,具体落实以工代赈,建设黄山事宜。许世英在黄山考察六天,所见所闻,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到上海后,他按照自己在山上的设想,尽其所能,不辞劳苦,多方奔波,筹款筹物,为黄山的建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一九三六年,正值日寇疯狂侵略中国之际,国民政府遣使乏人,许凭其在奉天任职期间与当时的日本驻奉天领事广田弘毅、副领事有田八郎的诗酒友情,居然在花甲之年慨然领职,由上海乘船前往日本赴任。
抵日后,初见时任日本首相的广田弘毅,即肯定公理,反对强权。及亲见天皇,又以“同根相护,燃萁煮豆”行谏,多方谋求调整中日邦交。但是一个“弱国”对强国的这种“劝谕”,无非是秋风过耳而已。期满一年回国述职前,他纵观日寇侵华野心不小,也曾庄严地向日方驻华使节重申前议,并电告中央,转饬平津严加防范。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深夜,许世英也曾因“无力回天”而电请辞职。五天后爆发卢沟桥事变,即刻放弃辞职之请,决心继任,七月十六日启程返日。抵日后敦告日方,要求其撤兵停战,并亲书“悬崖勒马”四字交付记者。日军侵入南京后,汉奸王揖唐两次派人到大使馆劝许飞回北平,均遭许严厉斥责,说:“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宜明大义,速即回头!”他认为:“事至今日,唯战可以复仇,唯守可以制胜,决不事谁而自取其辱。”次年初,许世英觉得对日已无外交可言,就怒降国旗,愤然回国。
回国后,就任全国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在各战区设救济处,下有难民收容所、收客站。他积极筹措难民救济工作,使不少因受战争摧残的难民得到救济,民间称赞他为“万民生佛”。
许世英在政坛纵横捭阖一生,而晚景却十分凄凉。从卸任驻日大使回国后,蒋介石政府任命他为国府委员,实则“尊而不重”。他怨愤至极,携妻带子前往香港闲居。由于他一生自律严谨,生活朴素,不置田产,晚年在香港生活困难,曾一度卖字为生。
据传,一九四九年北平筹备全国政协会议,周总理曾去电邀许世英回大陆,因夫人阻止,加上已经是耄耋之年,未能应约。一九五○年,遣其幼子许华回北京,参加革命。
一九五一年,许世英及其夫人姚依仁被国民党挟制去台湾,聘为“总统府资政”,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三日在台湾省台北市逝世,享年九十二岁。著有《许世英回忆录》、《治闽公牍》、《黄山揽胜集》等。
[4] 萧其煊(1890-?)——字叔宣,福建闽侯人。保定陆军学堂及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历任福州军务司课长、营长。北京陆军讲武堂教官等职。后留学日本陆军大学,一九二一年毕业回国,任奉军第二梯队参谋长。后任驻日本武官、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教育长。“七·七”事变一年后,投靠汪伪,任伪军上将,抗战后期在南京病死。